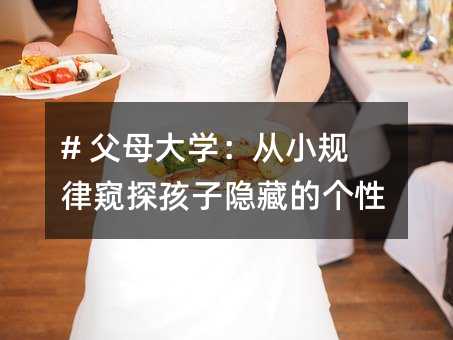“在国内是学渣,到了美国之后就变成了学霸” “出国的都是在国内混不下去的人”......虽然“洋高考考试”已经存在了不少年,但还是有很多的人对出国抱有不正确的态度和理念。但,伴随留学的低龄化愈演愈烈,留学生们所饱受的争议也愈加大。所以,在大洋彼端的孩子们,面对的角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逃不过的角逐
有数据显示,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舍弃国内高考考试乃至中考、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正以每年平均20%的速度增加。
依据教育部今年3月公布的数据,2015年度国内出国留学人总数52.37万人,其中自费留学48.18万人。与2014年度相比,出国留学人数增长了13.9%。同时,留学回国人数也增长了12.1%。
“洋高考考试”大热,留学队伍的结构飞速变化——愈加多初中生把美国的大学作为本科教育“目的地”;而为了上美国名校,很多学生在读初中或高中期间,便远涉重洋。
但父母花了大把钱把孩子送出去,真的可以让他们对接优质教育吗?还有,提早留学而躲开国内的应试教育模式,孩子真的就轻松了吗?
另一种角逐
“美国和中国,在哪儿读中学更辛苦?我逃过了中考、高考考试和应试教育模式,但其实角逐是逃避不了的。”
在耶鲁大学,记者遇见了硕士研究生李伟伦,她说起另一种角逐:“我总算分两步跨进了名校,但一路看到不少小留学生同伴选择舍弃。”
李伟伦是四川人,早在2004年读初中二年级时,就被爸爸妈妈送到美国东部一座城市。一家人的梦想,是期望她申请进入一所排名前50的美国大学读本科。但成绩全A的李伟伦,在角逐路上栽了个大跟头。
“在美国上高中,天天下午3点就放学了。但3点未来的自由时间,美国同学都安排得满满的,参加各种体育运动、社会服务、艺术类或科学类社团活动……”
事实上,美国当地的同学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就在为申请名校作筹备了,由于除去高中的学习成绩和SAT分数,美国的大学在录取新生时非常重视申请人的履历——一张履历表能否被填满,他们觉得这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个孩子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李伟伦对美国的升学行情一时没弄了解,况且融入当地环境要有一个过程,后来她也努力想参加社会服务等等,可是得花比其他人多得多的精力——譬如最简单的一件事,美国同学花20分钟就能在网上找到活动信息,她却要花上1个小时甚至更多。
“申请名校的本科,一个要紧录取指标是看你是不是展示出了领导才能。对我来讲,成为当地学生的领袖,显然非常难在高中三年里做到。”高中毕业前,李伟伦申请了15所全美排名前50的大学,结果一份录取公告书都没收到,只能去了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大学。
“进大学后,我重新分配了时间和精力,30%学习,40%社会服务,还有30%用来打造社会关系——最后在大学期间换来了一张填得满满的履历表。”4年努力,李伟伦取得了耶鲁的认同。
但在耶鲁念硕士,她心里别有滋味:“其实耶鲁如此的名牌大学,最看重的是本科生,第二是博士生,硕士生排在最后。”
李伟伦懂这类学历的不同含金量,不像国内很多人,一听“耶鲁”就立正,而且想当然地认定那里的博士肯定比本科生身价高。
有的名校的硕士项目,完全可以说是“创收”,“有些专业,硕士一招100多,而博士每年才招10个不到;硕士一年学费要四五万USD,而博士给奖学金,自己无需花一分钱。”李伟伦说,由于经济不景气,美国不少高校这两年都扩大了硕士招生规模,即使“常春藤名校”,也开设了过去十分不屑的1年制硕士项目,二三流大学新开的硕士项目更多。
百里挑一
在没到美国之前,像李伟伦如此觉得自己“一定拼得过美国同学”的国内尖子生,不少。这显然低估了美国名校入学角逐的激烈程度——它们让包含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海量国家的父母都“发疯了”。
择校,在美国孩子读高中、初中时,也是常见现象。
李伟伦说,要申请名牌大学,普通中学的学生总是吃点亏,除非你是学生中公认的领袖人物,甚至要在所在区域或所在州出类拔萃。美国人也相信,名牌中学有更多资源,尤其是拥有海量出色学生能造就更好的学校环境。名牌中学老师为申请人写的推荐信,对名牌大学是有说服力的。
“亚裔家庭看重孩子学业成绩已是世界闻名,但竭力帮助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一样是美国家庭的大事——这和肤色、国籍等等无关。”纽约史戴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的学生辅导员杰瑞米说。
史戴文森高中,是一所在全美能排进10强的公立高中。每年它的毕业生里,总有七八十名被康奈尔大学录取,二三十名被哈佛录取,二十名左右被麻省理工录取。难怪它是纽约州的父母“挤破头”也要帮孩子挤进来的学校。
史戴文森高中每年招生,都由纽约州统一命题考试,录取只看这次州考的成绩——也可说是“一考定终身”。过去,它的录取比率是100∶2或者100∶3,“后由来为经济不好,不少原本想送孩子上私立高中的人家也涌过来了,结果录取比率达到了100∶1。”杰瑞米说。
在美国入读好的高中,学业并不像国内传闻的那样轻松。“美国人不捧‘奥赛’,但好学校的学科困难程度一点不比‘奥赛’低。”而且,美国也充斥各种“冲刺班”、补习班和家教。“不少孩子到初二就要去上‘冲刺班’,为了考高中;考SAT前也上‘冲刺班’。只是白人圈子、亚裔圈子有各自追捧的辅导班。”一名刚被麻省理工录取的学生如此告诉记者。
美国名校比较多,不少家庭更倾向于让孩子选择离家较近的名校,譬如家在西海岸的多选西部名校、东海岸的更喜爱东部名校,另外每个州也有一些很好的州立大学,在本州读大学还免学费,所以不像国内大伙一窝蜂地只盯着少数几所名校。但这并不意味着角逐不激烈。
虽然所有名校都在招生广告中宣称:“欢迎每位感兴趣的学生选择加入。”但事实上,无论中外,永远只有前1%的尖子生才真的有“选择权”。
SAT高分,管不管用?
波士顿剑桥镇马萨诸塞大街77号,是小舟和记者见面的地方。大家身后,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地标建筑“大穹顶”。
“到了夏季,来学校的旅游团特别多,时常听到有导游在用中文解说。”伴随愈加多中国初中生“想到全美排名前50的大学读本科”,这种“励志之旅”正时尚。只不过,像麻省理工如此的名校,更想选择什么样的学生?小舟说,她是来到“大穹顶”之后才看透这件事情的。
她告诉了记者一个数字:20,“本科四届学生加起来,真的从国内考过来的,也就20出头。”
萃取
小舟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读本科,她非常了解,SAT高分根本不是她被录取和给予全额奖学金的重要原因。
她过去连续3年获得国际奥数金牌,曾是奥数国家集训队成员。虽然现在小舟非常不想说这个,但她了解:不挑明了,就不可以把不少高中生从“SAT的迷梦”中叫醒。
小舟出国前,家乡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争相报道她的事迹,但都“正确”地隐瞒了一个重点信息:从小学起她就进了奥数培训机构,然后同意了长达10多年的奥数练习——这会把不少人逼疯,却收获了像小舟如此真的热爱数学且有超强数学才能的人,也把她送进了世界名校。
“在这里,拿过各种国际大赛金牌的学生多的是,不稀奇。”小舟身边的那几个国内同胞,她赴美前就有印象,“有一个拿过物理金牌,比我高中一年级届;有两个先被北大录取,大二才来这里,也都是大家这种级别的‘选手’。”
生源是名校的生命线——这是一条“招生公理”,世界通行。名校招生,小舟形象地打了个比方,是在“萃取”:“美国名牌大学强调文化多样化、生源国际化,所以招生时会在世界各地、各种族、各民族的尖子生中按比率萃取若干。”
“风韵”
萃取,不一样的名校有不一样的标准。
当初申请学校时,小舟更心仪普林斯顿和哈佛,但被婉拒。她后来了解了:不同名校对学生各有“风韵”的需要,这一点恰恰最易被国内学生忽视。
“过去非常不服气,想不通为何被拒。”在波士顿剑桥镇,麻省理工学院跟哈佛大学紧挨着。小舟去隔壁的哈佛听过课,也日渐结识了不少哈佛的学生,最后想通了:“哈佛更喜欢招收有‘领袖风韵’的学生,果然,他们在大学里总忙着给自己组织的各类活动拉粉,总能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我真要去了那里,一定像个傻瓜,也会被烦死。”
性格沉稳文静的小舟,现在已经释然:除去分数、能力之类,各名校对学生的性格特点、专长更有很多细节需要,非常讲究精确度:“国内大学招生,是用考分做网眼、撒网打鱼;美国大学招生有点像钓鱼,而且只钓某几个品种。”
后来,还有人向记者道出了去美国念书才能了解的一个“文化秘密”:“美国不少名牌大学所称呼的‘校友’,并不包含硕士生和博士生。只有那些被精挑细选进去读本科的学生,才被觉得是‘校友’。”
学校根据“同气相求”的原则挑来本科生,而由他们体现、延续学校一贯的“风韵”。
弄了解了这类背景,再来看SAT高分,就不难了解:它管用,但程度有限。指望考得高分就进名校,那是中国式思维。
大部分没能进名校的中国学生,比较尴尬,“洋高考考试”没退路,只好往前走,“不少留学生一不小心就落到了三线大学或社区大学。当然,这对美国经济有利。”金融危机后,美国不少大学出现了财务危机,招揽留学生便成生财之道。“你在这里待久了,才了解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值得读,什么则是学校专门拿来谋财的。”
单说波士顿,就有近百所大学和学院,不少学校连当地美国人都不如何了解。这儿是美国“教育创收”的一个重镇,每年5月底6月初,波士顿全城的酒店房价总飚升得不靠谱,连坐落于远郊的汽车旅馆,都动辄开出每晚250USD以上的吓人价格,居然还一房难求。个中缘由,倒是波士顿人全都了解的:“这城里近百所学校都在办毕业典礼,毕业生的父母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
融合
在大洋的这一边,愈加多中国家庭为了孩子留洋,下决心“卖掉一套房”。但孩子要走的这条路上有什么样的风景,他们还不知道。正由于不知道,所以有种种美好的想象,兴致非常高。
“到美国读大学,最大的困难不是学业,而是融入当地社会。这非常难,真的非常难。”留美之前,不少过来人告诉小舟,比起读博士,读本科的一大好处是融入美国社会相对容易。但日复1日的生活,总不时在提醒小舟,“相对容易”跟“容易”不是一个意思。
譬如打麻将。当中国留学生围在一块玩“三国杀”,美国同学也在玩我们的牌。“有好几次,他们邀请我试着玩玩。我非常快熟知了他们玩的牌的每一条规则,但真的玩不到一块,感觉融不进来,别扭得非常。”
那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大家从小到大看过很多美国卡通片和电影,但来了之后居然发现,美国同学没看过,他们从小到大看的是另一些卡通片、电影和电视。玩牌时或其他时候哪个说一句逗笑的话,他们一听就乐开了,可我十有八九听不知道。”
在国内,不少人反对“低龄留学”,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和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都表达过差不多的怎么看: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并非小留学生可以随便适应的,“适应不了差异,会叫你在海外过得不好。”
而有的过来人看得更远,“过得不好”非常可能不仅仅是一段时间——所谓的“适应期”,也不仅仅是在海外的若干年。
“很多人还是想回国进步的,或者想留在海外却留不下来;而一旦回到中国,他们非常可能也会‘过得不好’。由于在海外待了那样多年,小留学生更是在观念、行为方法形成的关键时刻就待在海外,多少‘西化’了的人,回国后能否适应国内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又是一道坎!”
选专业,想法真不同
在国内,搏进名校的尖子生爱往经济、金融、管理等少数几个有“钱途”的专业扎堆。因此大学陷入了“半吊子教改”的困境:一方面鼓励学生根据兴趣选专业,同时提供中途改换专业的机会;其次却因为“热点专业”资源有限,不能不设置高高的门槛。
携带有关“热点专业”的中国式思维留学美国,留学生们对美国同龄人选专业的路数大为吃惊——想法真不同!
想法的差异,折射出种种深层次的差异。
“扬短避长”?
一年一度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前,小罗和爸爸妈妈一同来到哈佛校园,站在哈佛开创者约翰·哈佛的铜像前合影留念。
这是一家三口的“许愿之旅”。“本科申请哈佛太难了,将来来读个研究生吧。”眼下,小罗在读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的电子工程专业。
来美国读本科前,小罗在国内有过一段不太愉快的求学历程。这个北方小伙当年高考考试的第一志愿是上海交大,无奈几分之差,被北京一所二本院校的计算机系录取。爸爸妈妈焦灼于小罗“没上名校,出路堪忧”,便鼓励儿子退学留美。
虽然这一番折腾耗费了两年,但小罗感觉值:“我读的这个专业在全美排名靠前,将来不担忧找不到工作。”
电子工程、计算机等专业,由于就业前景好,是不少中国学生留美的最佳选择。
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专业,在全美乃至全世界都排名第一,研究生当中亚裔特别多,不少在中国名校读完本科的高材生来这里念博士。但在本科生中,这个专业并不炙手可热。选读经济系的本科生也不不少。
张旭,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研究生。一入学他就吃惊地发现,在选专业上“反时尚”的老美,大有人在。譬如,“有个哥们辛辛苦苦挤进去,理工科基础很好,却居然选了自己不如何懂的音乐系。他说音乐不止是音乐,也是一门技术活。”
中国学生坚信,扬长避短是在异国求学争取出类拔萃的不二法门,“过去读什么,来了这里还读什么,精益求精。”可能这就“谋杀”了个人进步的非常多种可能。
和美国同学谈就业选择,张旭感慨更多:“本来以为他们的目的是去Google、Microsoft如此的大公司,或者去华尔街,可发现根本不是。”美国同学心目中理想的公司,是刚刚起步、有潜力的小公司;而更多的人,根本不想去公司工作。
比尔·盖兹在麻省理工学院150周年校庆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曰“麻省理工为何出色?”
盖兹引述了一些广受追捧的数字,譬如这儿共有76个诺奖获得者;还展示了一些很多人没听说过的数字:这所大学的校友迄今总共创办了近26000家公司,合计有330万名职员,每年创造销售额2万亿USD。
“这里的科研环境非常浓,但它更是一所鼓励革新和创业的学校。”张旭正在慢慢适应麻省理工,他在中国留学生圈子里搞了一个平台,鼓励大伙也尝试创业,不要整日忙于考试、实验。
抛弃了“精髓”?
“不少中国学生向往耶鲁大学,但你会选耶鲁的什么专业?你了解耶鲁自己引以为豪的专业是什么?”周鹏从耶鲁大学硕士毕业,当然有了我们的察看结论:“耶鲁人真的骄傲的,从来不是经济学,更不是培养出了美国总统和最高法院法官的法学院。这里从教授到本科生,最津津乐道的是耶鲁有最好的艺术教育,戏剧非常棒,建筑学也非常棒……”
现在的网络上,中国网友可以看到各大美国名校的一些公开课程。尽管很多人惊喜,但间或也有人抱怨这类课程“含金量不够”,说“美国的大学其实不舍得开放那些真的优质的专业课”。
留美已七八年的周鹏告诉记者,对大学专业和大学教育的认知,展示着中美两国学生的差异。
“中国学生来美国,选专业大都跟找工作挂钩。譬如以前生物专业非常热,但目前读生物的人,连博士后也困难找工作,所以这个专业就冷了。”他感慨:“很不容易进了美国名牌大学,却不去汲取它的精髓,可惜了!”
在耶鲁就读期间跟一位执教艺术专业的教授的一次闲聊,让周鹏印象深刻。
“你以为这儿还是过去的耶鲁吗?她早就堕落了,被技术年代和商业社会的功利所侵蚀,大概只有中国人还感觉是天堂。”他们非常认真地说。
在今天的耶鲁,持这样批评态度的教授并不鲜见,“他们反感学校的一些做法,主要反对学校把过多经费拨给那些更能在短期内产出效益的应用类学科。”但周鹏了解,应用性越强、越容易找工作的专业,一向是中国留学生的“心头爱”。
“在美国,不少本科生真的在乎和感到自豪的,根本不是自己读什么专业,而是自己和其他人有哪些不同。”
周鹏的本科是在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的。这所学校在中国没什么知名度,可它的音乐专业在全美排名非常靠前。他忆起自己本科毕业前的最后一课——那是他首次被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震惊到。
“学校请来一位搞艺术的校友给大家上那一课。她讲的,是在欧柏林念书期间,她如何拒绝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最后给自己设计了一个专业,她要研究的居然是巫术。而大学居然允许她这么做了,最后还给了她学位!”周鹏说,此后他对美国教育多了关注和考虑,譬如教育环境和革新、个性、为学术而学术、让兴趣做主等等的关联。
当然,教育环境跟学生的求学动机关联更大。